评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从内亚视角谈法律多元主义与跨文明比较法制史的展望
评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
---------------------------------
——从内亚视角谈法律多元主义与跨文明比较法制史的展望
文 | 孔令伟

(本文作者孔令伟,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在今日的中国法制史学界中,原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寺田浩明可说是一位几乎无人不晓的代表人物。他关于中国法制史的著作,不仅史料功底扎实,且深有洞见。在大量且细致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寺田进一步对传统中国法,尤其是清代中国的法秩序,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总体见解,如为中国法制史学者所熟知的“非规则型法”(非ルール的な法)以及“拥挤列车模式”(満員電車のモデル)等理论性描述,对开辟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式,均多有贡献。寺田治中国法制史的著作,往往又围绕着两个核心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该如何立足于历史学的基础,适当地描述清代法秩序的实际运作方式?除此之外,当代的法学研究者该如何跳脱出以西方近代法为圭臬的偏见,进而通过中国与日本法制史研究重新定义前近代的“法”概念?这两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意识,也正是寺田近著《中国法制史》所关照的核心课题。
寺田《中国法制史》一书,除去序章与终章外,共分为八个章节,分别就“人与家”、“生业与财产”、“社会关系”、“秩序—纷争—诉讼”、“听讼”、“断罪”、“法—权力—社会”以及“传统中国法与近代法”等议题对中国法制史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后记,本书的写作基础实际上为寺田历年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部教授“中国法制史”、“东洋法制史”等课程讲义的总结修订;而这份课程讲义的总结,也反映出寺田本人的学术体系的架构。也由于本书各章节的内容,具有面向大学生与研究生课程的讲义性质,所以内容深入浅出、行文流畅,借由通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寺田的法史学体系有概要式的理解,也可以管窥日本大学法学部的基础学科教育内容。
总体而言,本书体大思精,比较全面地涉及了中国法制史中的诸多面向,又能深入浅出地利用清代法律文献对各议题进行精辟的阐发,无疑是一本近年法制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由于《中国法制史》涉及范围甚广,又由于笔者自身的学术背景所限,本文无意也不能对本书进行通盘的评价,而更倾向由历史学的立场,尤其是清朝史与内亚史的视野,为《中国法制史》的读者提供一些补充性的思考。
在序章中,寺田便开宗明义地提及本书的两点限制。首先是本书虽以中国法制史为题,实际上却是以清代法律的性质为主要讨论素材,寺田清楚地指出家族法、土地法、身份法、裁判制度与刑罚制度等议题随着中国历代的历史变迁,不可以立基于清代中国传统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逆推并笼统地概括,然而本书的用意在于以清代各类型的法律案例为出发,反映出中国历代法律发展的折射过程。有鉴于此,本书虽名为《中国法制史》,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理应具备独立的历史思辨力,不宜将作者以清代案例总结出的中国传统法特征,视为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中国法制史定律,否则极有可能陷入美国学者络德睦(TeemuRuskola)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亦即将中国法视为停滞不前的他者。笔者认为本书在时间维度上定义中国传统法时,之所以会无可避免地遭遇以清代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困难,实际上反映出中国法制史研究材料的核心问题,亦即清代以前中央司法档案与地方契约文书等史料的稀缺性,而这也是所有中国法制史研究者在试图建构跨断代的理论性论述时,所必须遭遇的主要问题。
关于寺田本书在时间维度上的限制,笔者一方面认为实属非战之罪,另一方面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即文献学与法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与对话。随着二十世纪初以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殷墟甲骨、周代金文、秦汉简牍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地下材料已成为中国史研究前沿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这些史料的相关研究,亦逐渐各自发展为甲骨学、简牍学与敦煌吐鲁番学等相对独立的学科;而这些地下材料研究的发展,如秦汉简牍研究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地方司法与民间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正为开拓中国法制史的历史纵深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然而由于断代史、文字学与文献学等专业门槛,要求所有的法制史研究者兼具甲骨、简牍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释读能力,显然并不实际。相反地,笔者在此更加想要强调的是,法学背景出身的法制史学者如何超越学科的藩篱,与精通甲骨、金文、简牍等地下材料的历史学与文献学同道展开实质对话,将是未来深化中国法制史维度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研究中国上古、中古、近世与近代等各个断代的法制史研究者,将来该如何展开跨断代的统合性研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除了时间维度上的限制外,本书亦具有地域与文化维度上的限制。寺田在序章中亦自承本书虽以清代法为主要考察对象,却无法包纳清朝特有的历史要素与地域差异,尤其是满洲、蒙古与八旗等清代法中的特殊因素。换句话说,寺田所定义的“中国”,本身具有地理与文化上的限制,亦即以中原地区与汉文化为“中国”法制史的代表,而以满蒙与汉军为核心的八旗制度以及通行于清代藏区与西北地区的佛教法与伊斯兰法,并不在其讨论范围之中。寺田虽在序章中直言了本书的限制,然而这并不代表其本人对于满、蒙、藏、伊斯兰等清代法中特殊因素的漠视;相反地,寺田的坦率或许反映出其对于清代法制史中民族因素的重视与开放态度。而寺田本人在京都大学法学部任教时,亦曾指导过清代蒙古法制史方向的研究生,如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环兼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清代蒙古法制史学者额定其劳(KhohchaharErdenchuluu)便是寺田的高足,由此可见寺田本人对清代蒙古法制史研究实有提携推动之功。额定其劳在京都大学求学时,亦曾编纂《蒙古法史日本语论文著作目录(1924~2008)》并于2009年刊登在当时寺田的研究室网页上,供相关研究者利用参考,对于促进蒙古法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侧面显示出寺田本人对于蒙古法研究的正面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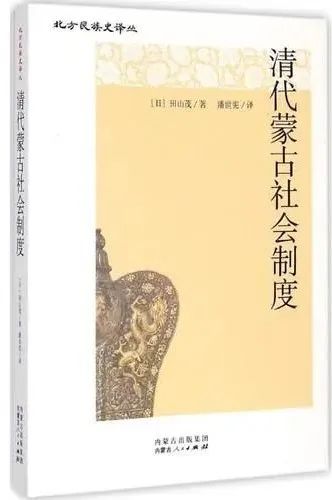
(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中译本书影)


(岛田正郎《北方欧亚法系通史》《西夏法典初探》书影)
事实上,日本法制史学界自二十世纪初以降,对于蒙古法史乃至于内亚法传统,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列举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日本的内亚法史研究中,以蒙古法研究为大宗,而田山茂是日本学术界较早关注蒙古法传统的学者之一,其相关代表著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法典研究》等。此外,原明治大学名誉教授岛田正郎也是一位具有指标性的人物,他在内亚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从契丹、女真、西夏的法律传统乃至于明清时期的蒙古法,均有所涉猎,其代表作如《北方欧亚法系之研究》《清朝蒙古例之研究》《明末清初蒙古法之研究》《清朝蒙古例实效性之研究》《北方欧亚法系通史》《西夏法典初探》等,可谓著作等身。除前辈学者外,目前日本青壮辈的学术骨干中亦不乏专研蒙古法制史的学者,如神户大学教授萩原守著有《清代蒙古的裁判与裁判文书》、东北大学教授冈洋树著有《清代蒙古蒙旗制度研究》,均属清代蒙古法制史不可多得之佳作。在以上较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法制史专著外,日本学者在发掘蒙古法律文书方面也有开创之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二木博史对蒙古文《白桦法典》的译注工作。碍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全面列举近年日本乃至于国际学界蒙古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考萩原守与额定其劳2014年所撰写的研究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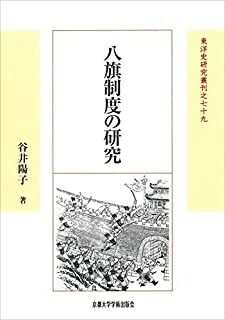
(谷井阳子《八旗制度研究》书影)
在蒙古法史之外,传统满洲法研究也是日本内亚法史研究的一大重心,其中又以八旗制度为重点,近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如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承志《大清国及其时代:帝国的形成与八旗社会》、天理大学教授谷井阳子《八旗制度研究》、东京大学准教授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等。在满文法制史史料开拓方面,有日本大学教授加藤直人对《逃人档》的译注研究,以及国士馆大学教授石桥崇雄等人对乾隆《钦定八旗则例》的题解介绍等相关成果。

(岛田正郎教授)
与中原内地、满蒙地区的法制史研究相比,日本学界中从事清代藏地与西北地区法制史研究的学者,数量上相对较少。总体而言,日本大学中的东洋法史教席,仍以中原内地传统法研究为主流;至于满蒙法史,则因二十世纪初日本的北进政策而获得较多关注,从而得以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传统。相形之下,日本学界中从事清代藏区与西北地区的法制史的研究者,尤其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宗教法方面,人数则相对较少,这主要可能是日本大学的学科建设所造成的。如明治大学名誉教授冈野诚,虽师从著名内亚法史学者岛田正郎并继承其教席,其学术贡献却以唐宋法制史文献为主,并没有承袭其师内亚法史的治学路线。根据冈野诚本人回忆,他在1971年的研究生入学面试时,曾对岛田正郎说将来想从事西藏法制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岛田则建议以研究传统中国法史为主,若有余力再研究西藏与蒙古法,因为研究内亚法史在日本大学中很难获得教职。这段故事也反映出日本法制史学界,长期以研究中原内地的传统法为主流,满蒙法研究次之,而中国藏区、西北地区与宗教法研究又次之的局面。
虽然日本学界中中国藏区、西北地区、藏传佛教与伊斯兰宗教法的研究者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却仍出版了不少质量优良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清代藏区法史方面,代表作如东京大学教授平野聪《清帝国与西藏问题:多民族统合的成立与瓦解》,除了专书以外亦有不少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如现任鸟取大学准教授、毕业自东京大学的柳静我,以及京都大学片桐宏道均曾撰写过相关博士论文。至于在清代新疆法史相关方面,前辈学者如原金泽大学名誉教授佐口透、甲南大学名誉教授堀直等人均有所建树,近年来东北学院大学小沼孝博与东京外国语大学准教授野田仁等人又有相关著作问世,为学界理解清代民族法规与新疆地方社会变迁等议题,皆有所助益。
除了內亚法史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层面外,近年来日本学界也有学者关注清代藏传佛教与伊斯兰宗教法等面向。在藏传佛教与法制方面,代表学者如早稻田大学教授石滨裕美子与关西大学准教授池尻阳子等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与扎萨克喇嘛制度等议题;在伊斯兰法方面,则有京都大学准教授中西竜也对清代汉人穆斯林社群法律传统的相关研究。
以上所列举之日文学界内亚法史研究中的既有成果,正如寺田在序言所言,并未被其统整纳入新作当中。然而本书既然以“中国法制史”为讨论范畴,而不使用范围较小的“清代内地法制史”,加上本书最初的预设读者又是刚入门的本科与研究生,不免容易使不熟悉中国通史、清史的入门读者有一种“中国传统法”等于“内地传统法”的错觉。
作为中国法制史的前辈学人,寺田对整体学科业已贡献良多,笔者在此的目的并非指出其近作之不足,而是站在后学的立场,希望自己与治中国法制史的同仁一同反思,未来的研究者该如何正视中国法制史中的多元面向,避免落入将“中国法制史”限缩于“清代中原法制史”的窠臼中?又该如何站在世界史的视野,将传统中国法与奥斯曼、俄罗斯各地的前近代法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摆脱一味以近代西欧法为普世价值的法律东方主义?而这也正是寺田在序章与终章中,对未来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提出的期许。本文以下将以寺田《中国法制史》部分章节内容为经,以内亚法史视野为纬,以期通过内亚传统法的研究实例,来深化寺田本书所提出的关键议题。
在第一章“人与家”中,寺田敏锐地考察了作为前近代中国法的基础社会单位“家”概念,尤其是同居共财、家产分割、尊卑长幼以及宗族观念等等。然而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本章所定义之传统中国的“家”概念,是一个根据清代内地经验所概括的原则性表述,无法充分解释清朝所统治的广袤内亚地区的社会基础。换言之,清代中国统治下满、蒙、藏等民族地区的社会基础,并不能用内地汉人的宗法与家庭概念来理解。例如适用于内地的《大清律例》,其刑律关于斗殴与故杀等部分,对于长幼亲属之间的暴力犯罪的惩罚,有很复杂的加减等系统,而这也反映出儒家文化亲疏尊卑的人伦思想。然而在清代《蒙古律例》中有关暴力犯罪的条文,却并没有如《大清律例》那般强调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亲疏关系,而是以“贵族—平人—家奴”的身份差异作为量刑加减等的基础,这也反映出清代蒙古法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根据“领主—属民”(eǰen—albatu)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非内地的宗法观念。
实际上,即便清代内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宗族观念并不适用于内亚地区,“家”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满、蒙、藏等地的传统法,尤其是对身份制社会下人身依附关系与法律实践的关联性,具有相当重要意涵。关于“家”一词,满文作“包”(boo);蒙古文作“格儿”(ger);藏文则为“囊”(nang),而由此又引申出“家人”的特殊含义,即作为家中依附人口的“奴婢”。如满文“包衣”(booi,意即“家里的”);蒙古文里则有“家人”(ger-ün kömün)、“家儿”(ger-ünköbegün);藏文的“郎生”(nangbzan,意即“家里养的”),这些称呼实际上所指的都是与家长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奴”,即家中的依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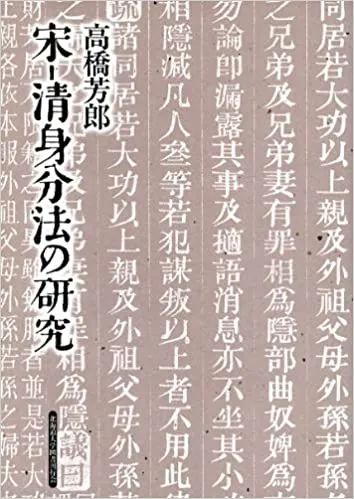
从上述满、蒙、藏等身份制社会中的“家”与人口依附关系的关系出发,可与清代家内奴婢、雇工人等依附人口的法律地位进行有趣的比较。寺田在第二章“生业与财产”中,曾参考高桥芳郎《宋—清身份法研究》的相关论述,对于清代一般平人的亲属律、奴婢律与雇工人律进行了深刻的比较,指出《大清律例》中奴婢和雇工人若殴伤主家尊长,需参照殴伤亲属尊长的原则加重量刑,这是考量到主人作为家长对于奴婢和雇工人等依附人口具有恩养关系。换句话说,清代雇佣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家内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就国家的良贱体系而言,作为良人的雇工人与奴婢在法理上有严格的区分,然而在法律的执行层面上雇工人却与奴婢处于相似的隶属层。就清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而言,由国家主导的良贱体系有所弱化,寺田亦注意到这可能与满洲人习惯中所存在的家奴有关,可惜并未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事实上,根据《清实录》等史料,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关于奴婢法律地位的变更,就是清廷试图以“满洲待奴仆之法”更改“汉人之俗”的一次改革。此后汉人奴婢如果有犯上、逃匿等情,“照满洲家人例治罪”;不仅如此,“典当雇工限内,及身隶门下为长随者,照满洲白契所买家人例治罪”。由此以降,汉人奴婢乃至于典当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被分别纳入“满洲家人例”与“满洲白契所买家人例”,而这也正式象征着就奴婢与雇工问题而言,清廷在雍正四年以满洲例取代明朝遗留旧制的历史进程。雍正四年上谕内阁中所提到的“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而且世世子孙,长远服役”,正是满洲人所谓的“世仆”(dangkan)观念,如康熙《满蒙清文鉴》云:“世代为奴者,谓之世仆”。对于雍正四年汉人奴婢适用满洲例的改革,《大清会典》中又多出一部分说明:“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属伊等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清册。”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满洲人“家生子”(ujin),如《满蒙清文鉴》曰:“包衣所生之子,谓之家生子”。由此可见,满洲法律传统中的“包衣”、“世仆”与“家生子”等概念,在雍正四年以后也被用于管理汉人奴婢甚至是典当雇工,对内地传统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不理解满洲文化语境中的“家”概念,就无从理解“包衣”、“世仆”与“家生子”等满洲例中的重要术语,也自然就无法深入探讨清代法制史中的满洲因素及其与内地传统法的交融过程。虽然对于以上议题,寺田本书中并未多涉及,然近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研究清代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关注旗人的法律地位及清代中国法制史中的满洲因素,这点或许也反映出中国法制史研究朝向多元化发展,而不再只是关注内地传统法的未来趋势。
在第二章的后半节中,寺田详细地介绍了租佃关系与土地所有制,但是如同其先前对于奴婢与雇工人的论述,本书对于官庄、旗地与庄头等清代土地法中关键的满洲因素,依旧是着墨不多。寺田在此讨论租佃关系与管业来历的目的,主要还是试图通过“业”这个关键词,将传统中国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做概念上的梳理,进而与西方近代法中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比较。寺田所讨论的土地制度,主要仍是以清代的案例为出发,却没有讨论在华北地区占据大量土地的旗人社会。实际上,在1644年清朝入关以后,在清廷的允许下,旗人通过圈地与投充在华北地区占领了极为广袤的土地,并以满洲固有的旗地与庄园制度进行土地管理。这些旗人所拥有的土地,性质与一般汉人民地极不相同,不仅是由内务府或八旗王公而非地方官府所管辖,庄园土地亦不可自由进行市场交易。而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在皇室宗亲与八旗王公手中,实际的管理者却多半为作为土地所有者家奴的庄头(满文jangturi)与园头(满文yafan i da)等人。而这些具有家奴性质的庄园旗人因为世仆,而人身属性与一般民人地主并不相同,不仅人身自由受到主仆关系的严格限制,即便是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也取决于主人的态度。这些在畿辅地区占据庞大土地的旗人社会,其土地观念与所有权秩序,与一般汉人民地截然不同,尤其是八旗王公与庄头之间立基在主仆观念之上的土地关系,无法以中原传统法的租佃关系与管业来历等模式一概而论,而是必须回归到满洲固有的人身依附与土地观念来理解。关于以上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邱源媛的近期研究。

在第三章“社会关系”中,寺田总结了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中地理论来讨论传统中国的市场网络,并提及宗亲会、同乡会与秘密结社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寺田根据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制作、加工了一张地图,但由于施建雅模型本身并未将蒙古、藏地与新疆等地纳入讨论范围,因此清代统治下的民族地区在本章中再次被略过。如前所述,内亚地区并没有华南汉人社会中那样的“宗族”概念,因此相对于汉文化中宗亲会与同乡会等血缘与地缘组织,蒙、藏、疆等清代民族地区中宗教寺院组织扮演着社会网络的枢纽。由于十六世纪末以降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取得的主导地位,佛教寺院不仅得以累积大量的属人与土地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更成通过经院教育与举行法会等宗教活动成为地方社会共同体的精神中心。这些蒙藏地区的佛教寺院,不仅有着相对严密的宗教法规(藏文bca’ yig;蒙古文ǰayiγ)以维持其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施供关系(藏文mchod yon)的佛教理论与地方势力甚至是朝廷中央有所联系,进而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原汉人社会的宗亲会与民间信仰团体有着结构上的本质区别。而上述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实际上也影响了清代内亚地区的汉人社会,例如在喀尔喀蒙古地区便有不少汉人移民投靠哲布尊丹巴所辖寺院而成为其属人,使得这些汉人的法律地位乃至于身份认同产生了关键的变化。而甘青地区藏地佛教寺院与地方氏族势力的政教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也影响了清朝针对当地寺庙制定的规范以及边疆政策。除了蒙藏寺院所使用的佛教法规外,西北地区所盛行的伊斯兰教沙里亚(Shari'ah)法以及清真寺与麻扎等宗教组织亦是研究当地社会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汉人社会网络中所盛行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并不能用来深入理解内亚地方社会的法律实践,而是应该考察佛教与伊斯兰教宗教团体及其宗教法传统对建构地方团体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第四、五、六章中,本书重点通过清代中原地方档案讨论诉讼、听讼与断罪等司法审判议题。在讨论清代国家行政与裁判机构时,寺田列出了一张图表,相对清晰地表现出皇帝、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地方督抚与府州县之间的层级关系;然而这张图表中,却并没有列入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扎萨克、各地驻防将军与驻藏大臣等重要裁判机构。由此可见,本书在讨论所谓清代的国家裁判体系时,其范围仅限缩在中原地区的汉人族群,不仅没有涉及作为清朝统治核心的旗人,同时对于外藩蒙古、藏人以及突厥语系穆斯林等非汉族群,均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本书关于司法审判与诉讼部分的讨论,似乎也仅适用于清代中原部分地区,并不能用来理解直隶的旗人与蒙藏疆地方的法律实情。如读者想进一步比较清代中原与民族地区司法审判的异同,近年来利用清代内亚地区多语地方档案研究司法审判等相关议题,亦有不少新兴研究发表,在此仅列其一二。如在清代京控与光棍例等中央司法制度中,回民与旗下人等多元因素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可参考李典蓉的研究成果。理藩院审判职能的形成,则有Dorothea Heuschert-Laage近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清代蒙古盟旗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制度,可以参考额定其劳与蒙古勒呼的相关论文。至于清朝司法制度在在安多藏区的继受以及与地方传统的交融转化,可以参考马海云与欧麦高(Max Oidtmann)的相关研究。
在第七、八与最终章中,本书从中国传统法的习惯、契约等基本核心概念出发提升到与西方近代法进行概念比较的理论层面,并提出寻求覆盖世界史的法概念以寻求比较法制史的主张。而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法制史研究如果能超越以“中原传统法”笼统概括“中国传统法”的刻板印象,进一步正视中国法制史中满、蒙、藏、伊斯兰等多元因素,将极有助于比较法制史的开展工作。寺田本书在法的类型学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研究框架与问题意识,值得后学追比;然而在研究对象与史料取材方面,本书的写作范围与其说是“中国法制史”,不如说更像是“清代中原法制史”,而这个现象实际上也片面体现出中国法制史学界长期“重中原、轻内亚”的研究范式。其实不只是满、蒙、藏等内亚地区,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也有独具一格的传统法,如乾隆元年(1736)年平定苗乱后,清廷为符合现实统治需求,乾隆帝便明令:“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这显示出内地传统法并无法用来充分理解清代苗疆的法律实践。
实际上,清朝对于满洲、蒙古、西藏、新疆乃至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一方面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式,将民族地区习惯纳入地方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也吸收民族地区在历史时期所发展出的成文法,进而将其制度化,因此在民族地区制定了与内地有所区别的法律规范。清朝这种在大一统国家体制下尊重各民族传统法与习惯的治理方式,可以被理解为近年法律史学界兴起的“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亦即一个国家体制内,可以包纳多元的法传统,进而形成大一统的重层体国家。就这点而言,清朝与包纳多元法律传统的奥斯曼以及俄罗斯帝国具有相似性,通过重视清代中国的“法律多元主义”,亦即将满、蒙、藏、伊斯兰等多元法律传统与内地传统法等量齐观,以法制史为切入点将清朝、奥斯曼与俄罗斯帝国进行比较研究,正可为寺田在终章中所强调跨文明比较法制史的愿景,提供极佳的实践可能。总体而言,寺田《中国法制史》一书通过立基于清代汉文中央史料以及中原地方档案,为开展中国法制史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而未来的研究者们如何站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共同合作整理汉、满、蒙、藏、察合台文等多语种法律文书,进一步展开跨断代、跨学科乃至于跨文明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将是学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68-681页,注释从略。推送版本可能与纸本有所不同,若需引用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投稿方式说明
承蒙学界同仁的提携与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业已出版15辑,投稿方式如下:
来稿请以纸版或电子版方式,分别寄至:
(100088) 北京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编辑部
电子邮箱:
gdflwxyj@outlook.com
gdflwxyj@163.com
每辑的截稿时间为当年6月30日。
谨此奉闻,诚盼赐稿。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编辑部
欢迎关注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获取更多学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