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自1999年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突破学科划分的藩篱,努力实践多元化学术路径的整合,是学界率先出版的以法律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为适应信息时代学术传播载体多元化的趋势,本刊编辑部决定以“法律史料整理与介绍”“先秦法律史研究”“秦汉法律史研究”“唐宋法律史研究”“明清法律史研究”“域外法律史研究”六个专题,分类推送往期各辑刊登的相关论文、述评以及书评,以备学界同仁参考。
今年十二月十六日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名宿A. F. P.何四维(Ahthong Francois Paulus Hulsewe)先生逝世十周年。何四维先生以其在秦汉法制史尤其是秦汉法律文献研究中所做出的业绩而广为学界所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何四维先生因心脏麻痹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一九九五年一月,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温先生在《东方学》第八十九辑上发表了追忆文章,对何四维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业绩作了较完整的介绍。值此何四维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经池田温先生同意,我们将此文译出(稍作节略),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何四维先生。
以荷兰中国学的长老、秦汉法制史专家而知名,又以莱顿大学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通报》的编辑者而多年来一直活跃的何四维氏,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因心脏麻痹,在他退休后一直隐居的瑞士罗蒙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东方学会曾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邀请何氏访问日本两周,在东京、京都举行了讲演会与恳谈会,获得了日本与荷兰学术交流及友好的机会,并由此了解到了何氏博洽精细底蕴之一端,同时也感受到了他那充满幽默、认真的性格。现在此追思何氏生前的学术业绩,从内心表示哀悼之意。何氏访日之际,在东京与京都用英语所作的学术讲演稿,已由樓一雄、藤枝晃氏译成日语,以下述标题刊登在本刊第四十七辑(一九七四年一月):《汉书卷六十一与史记卷一百二十三的关系》(第一一九〜一三三页),《汉代绢贸易的要因》(第一〇四〜一一八页)。
何四维氏一九一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随荷兰籍双亲出生于柏林。父亲的祖先自十七世纪以来在格罗宁根世袭荷兰新教教会牧师,至祖父一辈转事农业,父亲则为电力技师,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九年供职于德国阿隆电力器具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避食物不足之忧,除去在伯母居住的阿纳姆生活了两年,一直在柏林就读小学,体验了德语与母语荷兰语的双语生活。这对长于外语、至少可以自由使用六国语言的他的人格形成,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全家返回荷兰,一九二七年中学毕业。在这期间于阿姆斯特丹东南郊外的比瑟姆度过了幸福的小学、中学时代,喜欢读卡尔迈(Karl May)和朱尔斯•维恩(Jules Verne)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夏,曾与两名学友步行至莱茵河,从那里或徒步,或乘船,用不足一百荷兰盾愉快地旅行至海德尔堡。青年何四维的最初理想是做一名教师,以后逐渐对文科产生兴趣,为准备考试而学习了希腊语与拉丁语。此后参加了荷兰管辖下的东印度政厅的培养文官奖学生(主攻中文、日语)考试,通过竞争而合格。
自一九二八年秋,他在莱顿大学与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法学者的范•德尔•瓦尔克(M. H. van der Valk)一起,跟随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德伊文达克(J.J.L.Duyvendak,戴文达(一八八九〜一九五四)学习以《四书》为教材的古代汉语,同时向福建方言助手张廷特塞(Ch’ang Tientse)学习现代汉语与兰印华侨所说的厦门方言,又学习了十册日语小学课本。学习最初在大学图书馆的汉语室与戴文达的家中进行。一九三〇年,位于旧大学楼旁占有两间独立的房间的汉学研究所建成,众多的汉文图书自图书馆移藏于此,使学生也得以利用。作为新同学,以后《唐与唐以前的绘画论》的作者、美国人W.R.B.阿克(W.R.B.Acker)也参与其中。阿克向何四维学习德语,何四维利用剃须所用的镜子指导他如何正确发音。一九三一年兰印政府文官候补者考试合格后,与印尼语学生C.曼丝(C.Mans)小姐结婚,共同前往中国留学。经一九三二年一月爆发的上海事件的所在地上海,于一月三十一日到达大沽,开始了约两年时间的北京留学生活。
最初他感到在阅读文学作品与书写中文方面并无障碍,但尚不能使用日常用语,因此主要跟随满人先生学习会话。开始住在位于东四头条胡同的华北语言学校,夏天至西山大觉寺避暑,后迁至建国门内的西裱褶胡同。他对不属于特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在市井中学习汉语并体验中国生活文化的生活,感到非常高兴。他曾与同学范•德尔•瓦尔克一起,与梁启超之弟、古典学者梁启雄交友,在北京图书馆内梁氏房屋中共读《左传》、《史记》,又从满人先生读老舍的《赵子曰》。范•德尔•瓦尔克学习中国现代法,劝他研究中国法制史,以此为契机,他着手翻译旧、新两唐书《刑法志》并以此作为研究课题。一九三三年初,旧友&阿克从日本来到北京,二人结伴前往太原旅行。他与美国留学生德克•卜德(Derk Bodde)交游并成为终生好友。至晚年时,他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给卜德的长信中,详细叙述了胡同里的各种卖货车与工具,从叫卖声到色彩丰富的婚礼及葬礼队列,从商店街的招牌到季节性食物等,对旧京风物的强烈怀旧之情跃然纸上,哀叹它们消失于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何氏在北京留学期间,因对弓术感兴趣而有所学习。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离开北京,前往下一个留学目的地日本。他在日本停留一年,主要居住在京都,旅行足迹涉及本州各地直至北海道,富士山上也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京都居住在只有塌塌米的纯日式木结构房屋,屋内挂着中国画并摆放着壶。一米九十的身高触天花板,而吃饭必须在仅二十五厘米高的食桌上取拿食物。房屋与柜子的拉门上,画有灰色的饰物与仙鹤、芦苇。冬天只有几个火盆与小煤油炉。他自己穿藏青色的棉布和服,备有黑袜、木屐,能够身穿和服行走。他努力通过日本生活而习得日语。已然久违的在莱顿的泛读学习又从头开始,他请了Kurohatitose小姐为个人教授,又与曾和Albert Koop合著英文《铭字便览Japanes names and how to read them. Amanual for art collectors. 》(伦敦,一九二〇年)的稻田穗太郎一起阅读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遗》序,这是与他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一环。在日本,他与B. 阿克再度相逢,对弓术的兴趣也得以延续,跟随那须与一的后裔学习日本弓道。
一九三五年新春,他乘船离开日本,前往任职地巴塔维亚。在当地被分配到荷印政厅东亚局的日本局,主要从事通过中国、日本的报纸杂志,搜集并向政厅提供关于东亚政治、经济、社会动向情报的工作。何四维等人自此至珍珠湾事件期间的工作情况,R.D.哈斯鲁(R.D.Hasloch)Nishi no Kzaze, hare (Weesp, Van Kampen, 1985年)有具体记载。他的起居规律是,上午七点半上班,下午二点下班,回家洗浴,吃罢热午餐后午睡。晚上吃冷餐,较早就寝。在这一时期,他游历了苏门答腊与巴达维亚附近的千岛湾、中部爪哇岛遗迹,阅读了所喜爱的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的《好伙伴》与C.S.福雷斯特(C.S.Forester)的Homblower stories及S.拉格勒夫(S.Lagerlof)的Nils Holgersson,带领一男二女去动物园,以年轻的殖民地官吏度过了安定的生活。一九三九年获得长假回国,进行了以汉语为主、日本文化史为副的最终资格考试的准备,提出的论文题目确定为“旧唐书刑法志译注”,并完成了七十一页的工作。
同年十月返回任职地。翌年,一九四〇年五月,荷兰遭受德军侵略,政局为之一变。兰印政厅设置了检阅局,他被调任于此。据他自己概算,在那里他过目了约二万五千封以上的日文书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对美、英、荷宣战,荷印亦卷入战火之中。在开战前,他因担心前途而将中国画送至在美国的叔叔家,除此之外,在北京购买并带回来的物品悉数丧失。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被任命为海军中尉,受命被派往总督所在的万隆,五月八日以翻译的身份在受降现场。他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其文作为资料被收入官方编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荷兰》(L.de Jong, vol Ila, Nederlande-Indii, 1, part1, chap.1; Surrender, ppv.1-8),曾持续了四个世纪的荷兰殖民地统治在事实上结束。作为军人而被俘的何四维与同伴一起,于一九四二年岁暮被送往新加坡。包括他全家在内的俘虏的命运,在他的友人、心理学教授N.比茨(N.Beets)所著的De Verre Oorlog (Meppel, 1981年)有详细叙述。由于身患赤痢,他被免于修建铁路的苦役,与三个荷兰人一起进入阿格姆公园的别墅,在一间大房间内翻译与新西兰相关的荷兰文出版物。不久又转移到Saimorodo。的空军宿舍,与其他小组合并。新加坡的俘虏生活对他而言,在来自帕斯的校长及丹麦人医生、英国演员的关照下,成为有益的经历。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在章宜监狱度日。
战后,他作为翻译去往泗水,为荷兰海军劝说日本人安全保留海军基地,但是日本人未从,他们被蜂拥而起的印尼人徒党引渡回了印尼。当时确系万分危机之时,他被告知第二天将被斩首,并被关入像狮子笼一样的水泥地面的小屋。所幸第二天早晨暴徒并未返回,他得以保全性命。他被英军救出后送至新加坡,以后在《东南亚华侨》一书的作者韦格达•帕塞(Vikuta Paseru)的手下,在英国陆军司令官的华侨局工作了数月。一九四六年二月,荷兰海军将其召回巴达维亚,但不久即因病与家属回归本国,分配至哈格海军参谋本部的情报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戴文达教授与他取得联系,教授告诉他,他已经拒绝了牛津大学的邀请,而向莱顿大学表示了留任意向,对此大学将向他提供一名讲师的职位,教授问他是否能够担当此职。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不久,在戴文达教授的努力下,他正式向海军与荷印政厅辞职,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莱顿大学担任教职。
两年后,他的研究课题由唐代与唐律转向汉代。其理由之一,就是卡尔-宾格尔(Karl Bunger)的《唐代法史资料渊源》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te der Tangzeit于一九四六年刊行,他为他的课题已被他人先行研究而感到吃惊并失望,不过最积极的理由是其师戴文达对汉代浓厚的兴趣也使他的注意力倾向于此。戴文达的高足E.M.格雷(E.M.Gale)与D.卜德(D.Bodde),已经撰写了有关汉代问题的博士论文,他的美国朋友、牛津大学教授杜布斯(Dubs)英译的《西汉十帝本纪》也于当时刊行。另一方面,成为他汉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M.韦伯(M.Wilbur)的《奴隶制研究》与南希•李斯万(Nancy Lee Swann)的《食货志译注》的出版也与此相关。他的老师也向弟子们——Tjan Tjoe Som、R.P.科迈尔(R.P.Kramer)、P.范•德尔伦(P.vanderLoon)与何四维建议翻译《汉书》的各个部分。于是他决心翻译《汉书•刑法志》,并搜集了《汉书》与汉代文献所反映的法律制度,于一九五五年完成学位论文《汉律拾遗》。
一九五四年戴文达病逝,他于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继任为教授。此时,他与生有一男三女的夫人离婚,与玛格丽特•瓦兹尼斯卡(Marguerite Wazniewski)女士再婚。以后直至引退,他度过了二十年充实的教授生活,培养了数量虽然不多,但每年连续不断的学生,接连发表论文与书评,不得闲暇。他的就任讲演以“唐代的死刑执行与禁杀戮期间”、“中国社会史散策”(荷兰语)为内容,以后则以汉代法制为焦点,一以贯之地以广阔的视野深入历史研究。他努力排除先入观念的束缚,将热情倾注在依据史料复原历史之中。
众所周知,他与保罗•德米耶维尔(Paul Demieville)合作,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担任了在荷兰颇具传统的中国学杂志,同时也是研究中国的国际性杂志,著名的《通报》主编,为此倾注精力。一九四七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居住数月,自此以后,他通过参加众多的学术会议与讲演,尽力于中国研究的国际协作。如一九六三年夏,他在华盛顿大学参加了三个月的汉史教学;一九六五年夏,W.F.莫特(W.F.Motr)教授出差,他作为代理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一九六五年他获得带薪休假,重访中国与日本进行了学术交流。
一九七五年自莱顿大学退职,获名誉教授称号。退休之际,莱顿大学为了纪念他,举行了题为“汉代的国家与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汇集的论文以后有若干篇使《通报》凭添声色。退休后他离开莱顿,迁居义母所在的瑞士弗莱堡以南的小乡镇罗蒙,专心研究著述。从教授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在无任何事务纷扰的静谧的环境中,他得以深度加工、思索多年来积累的资料,进入整理汉代法制于西域经营研究的阶段。受一九七七年遭遇车祸的影响,去欧洲各地游历的次数逐渐减少。
七十年代后半期,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写有秦律的竹简,这批资料的公布更激发起他的研究欲望。于是产生了《中亚中国——初期前一二五年〜二十三年》(一九七九年)、《秦律遗存》(一九八五年)这两部著作,另有论考不断地刊登在学术界的杂志上。一九八九年七月,日本人研究生以秦简为题写了五百页的学位论文,请他审阅,他用了一周的时间认真阅读了以瑞典语写成的论文,并撰写了恳切的评语。
一九九〇年迎来了八十岁诞辰,他的高足W. L. 艾德马(W. L. Idema)和E.齐歇尔(E. Zurcher)两人以“秦汉中国的思想与法”(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China. Studies presented to Anthony Hulsew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E.J.Brill,1990,ix+244pp.)为题,合编了纪念文集奉献给他。文集中包括了以他的弟子为中心,同时也包含朋友在内的十二人的得意之作,并附有他的传记与网罗性的著作目录。
传记由一九六八年入莱顿大学师从何四维学习汉语的学生,活动于现实社会的菲利普•德尔•海尔(Philip de Heer)执笔,其中频繁地引用了毕业后师生间的来往信函,是文学性很强的名文。本文基本上参照该文,只限于在大幅度删略的基础述其梗概。
以下为收入前述论文集中,由德尔•海尔氏编纂的著作目录。三部代表作之后,附有可资参考的若干书评类文章。此外考虑到读者方便,中国与日本的人名、书名将以汉字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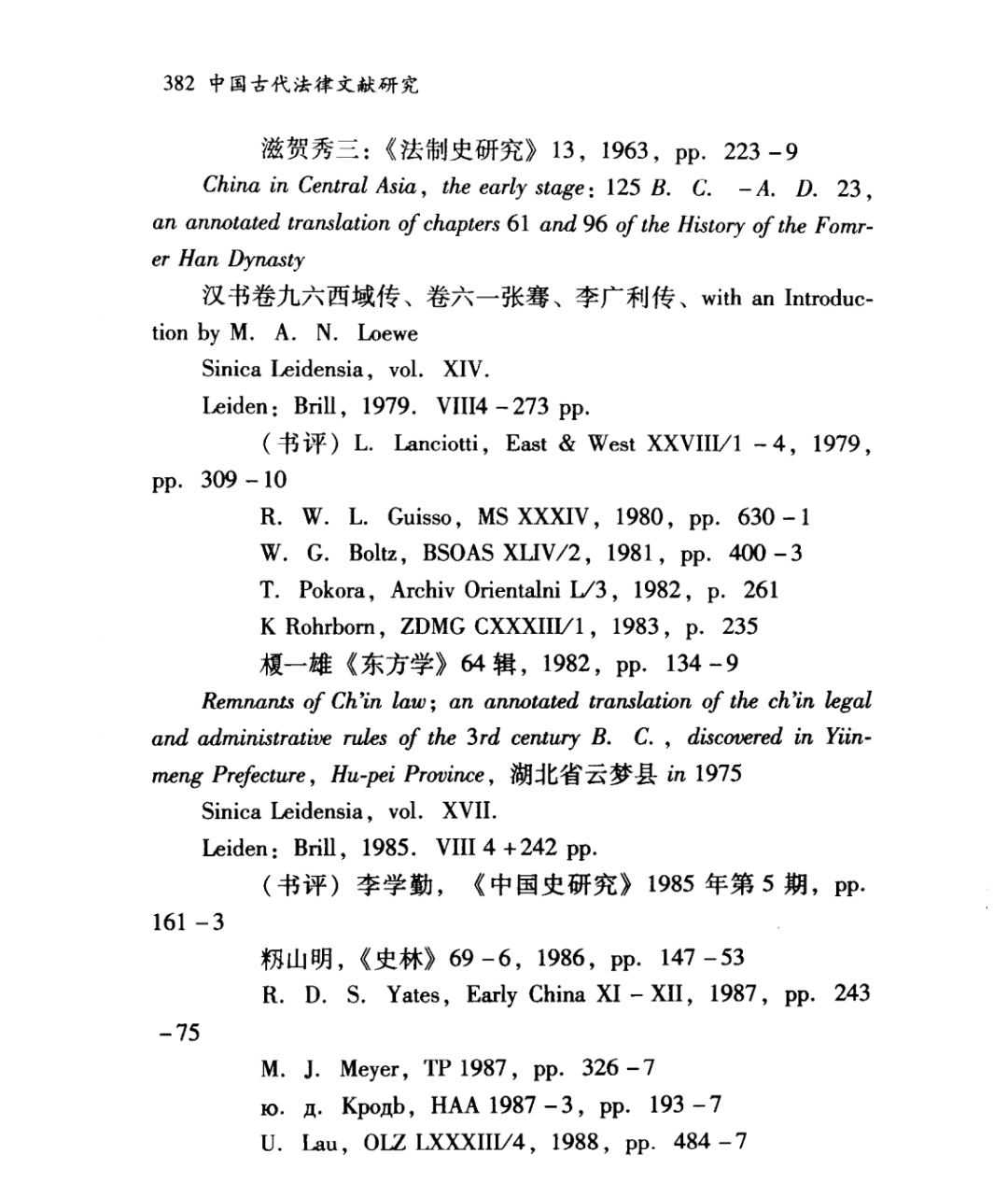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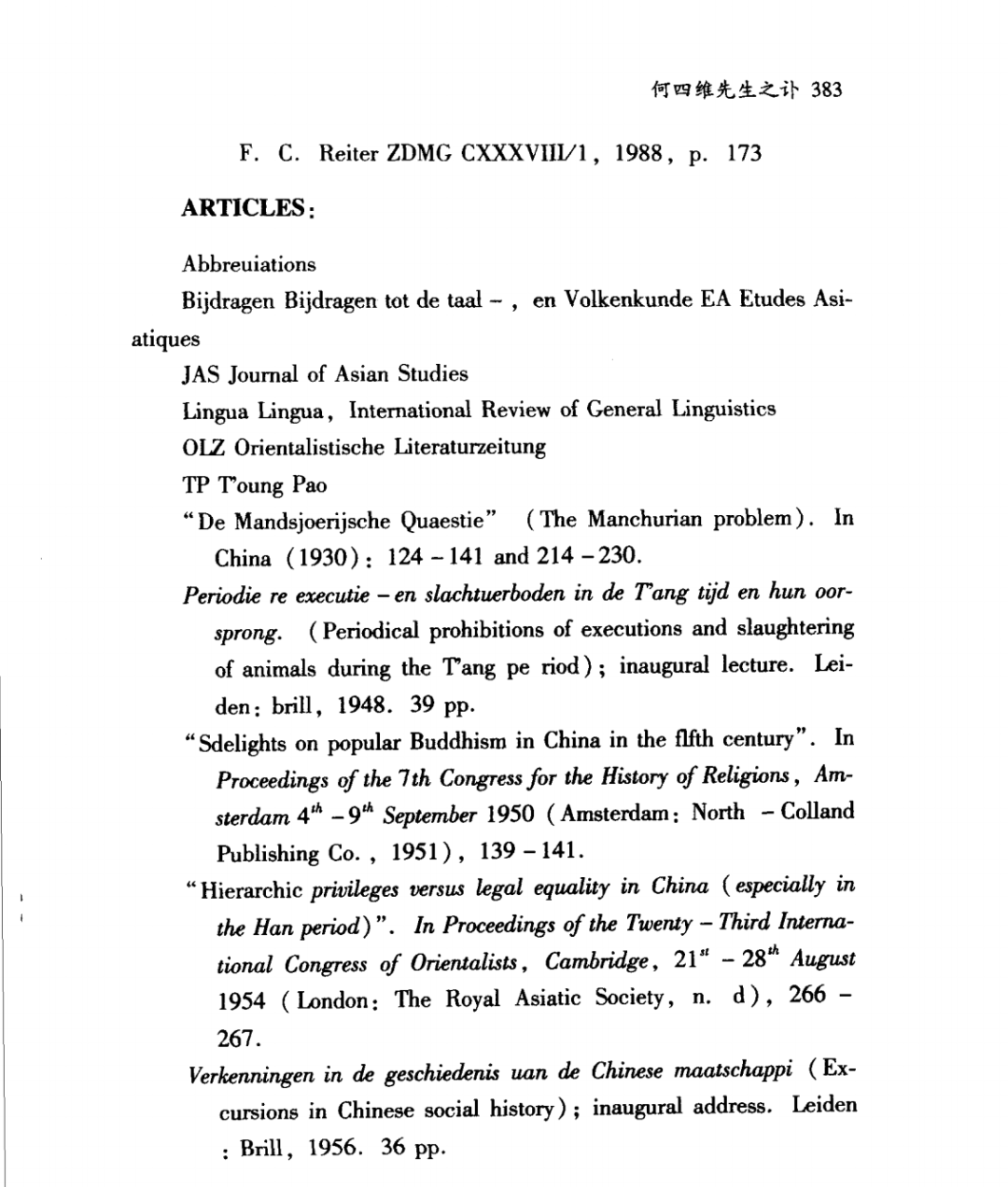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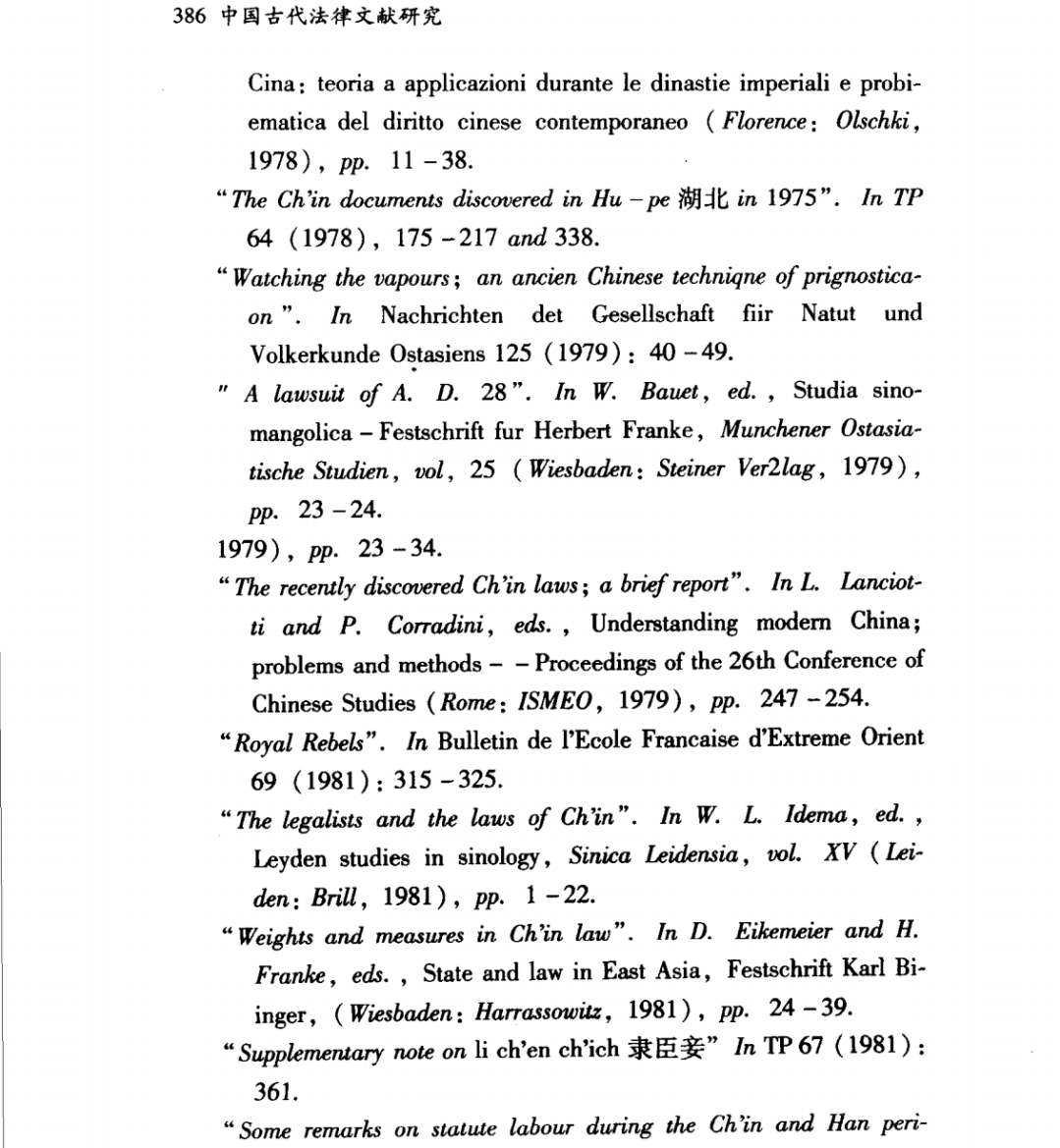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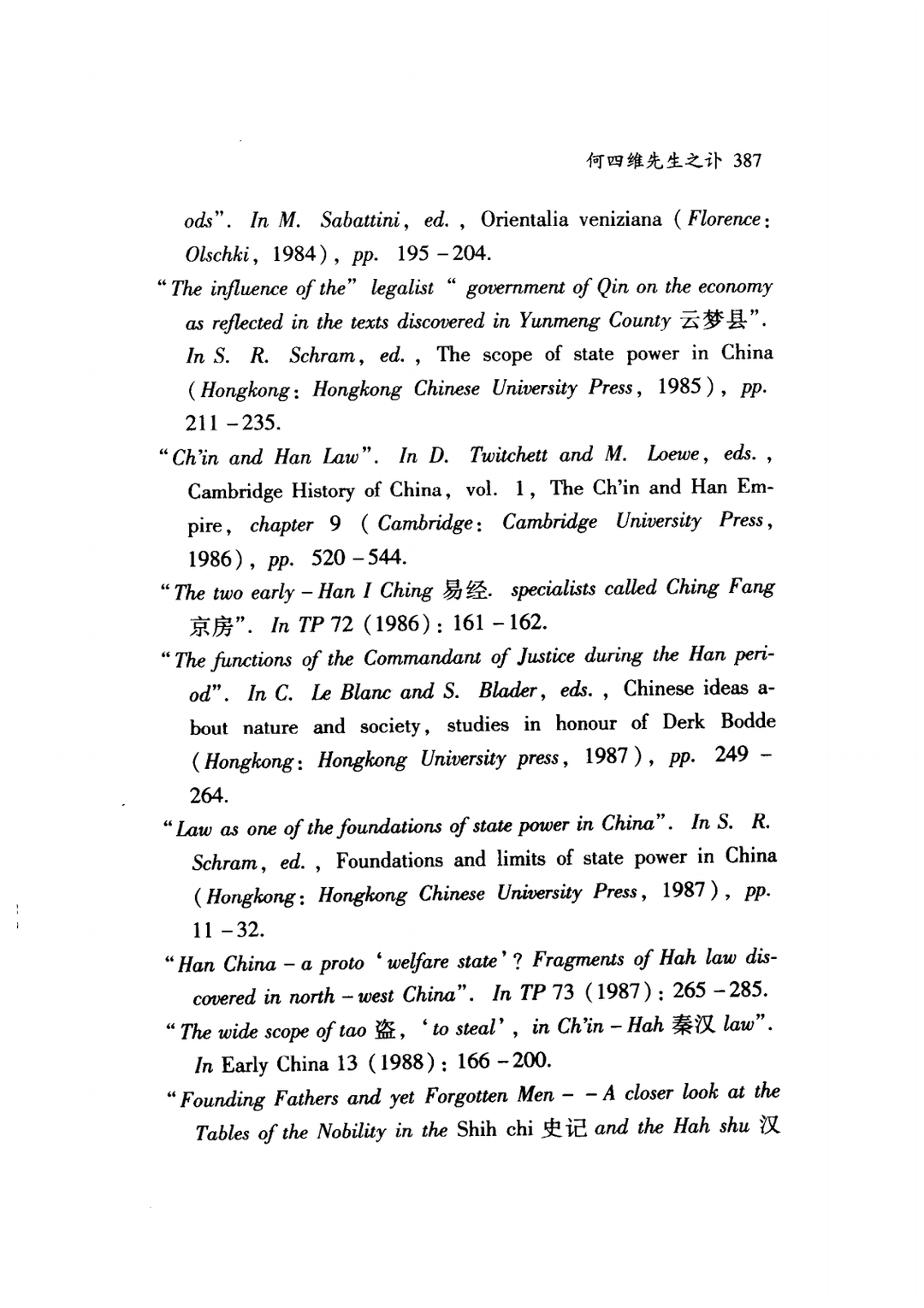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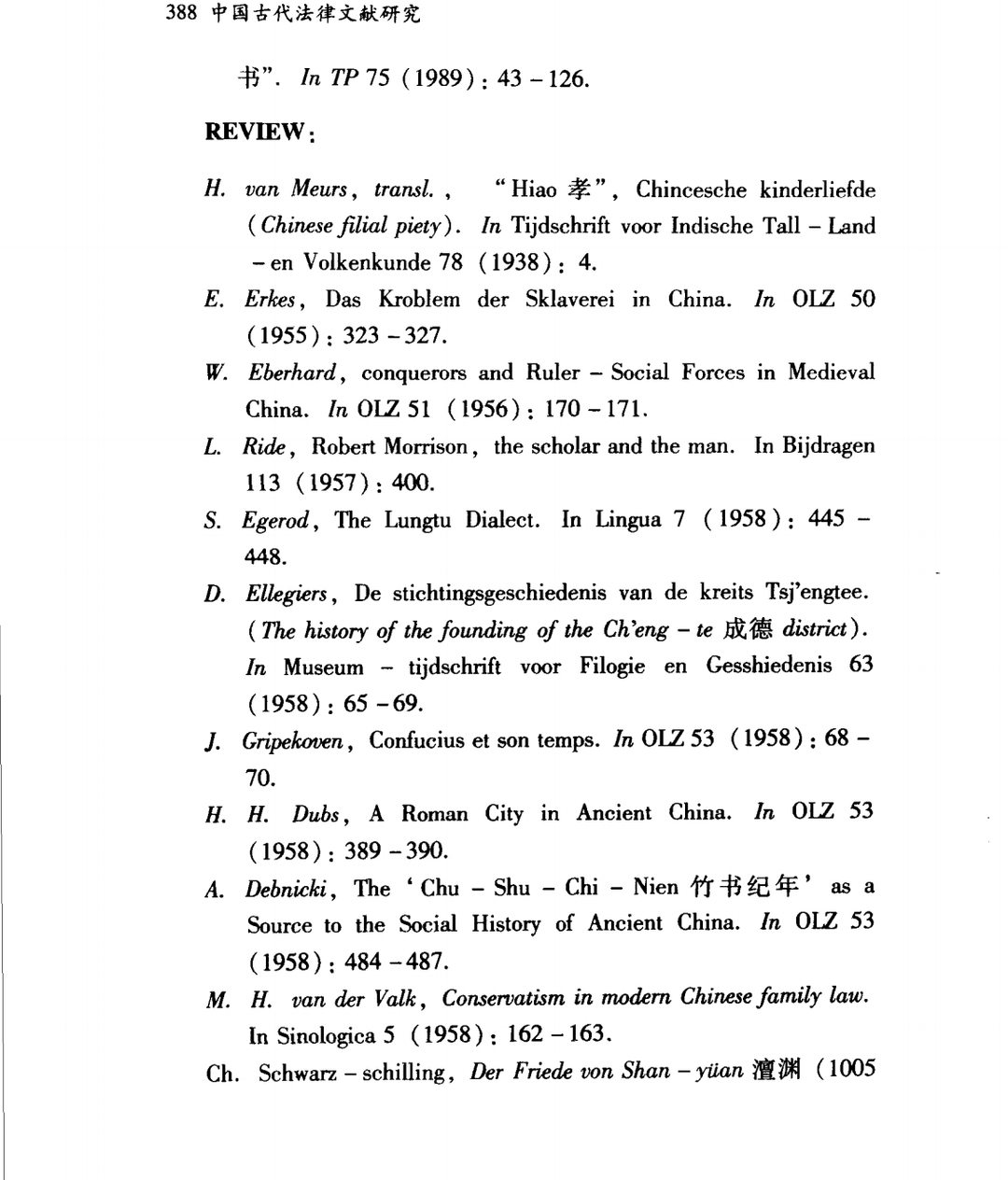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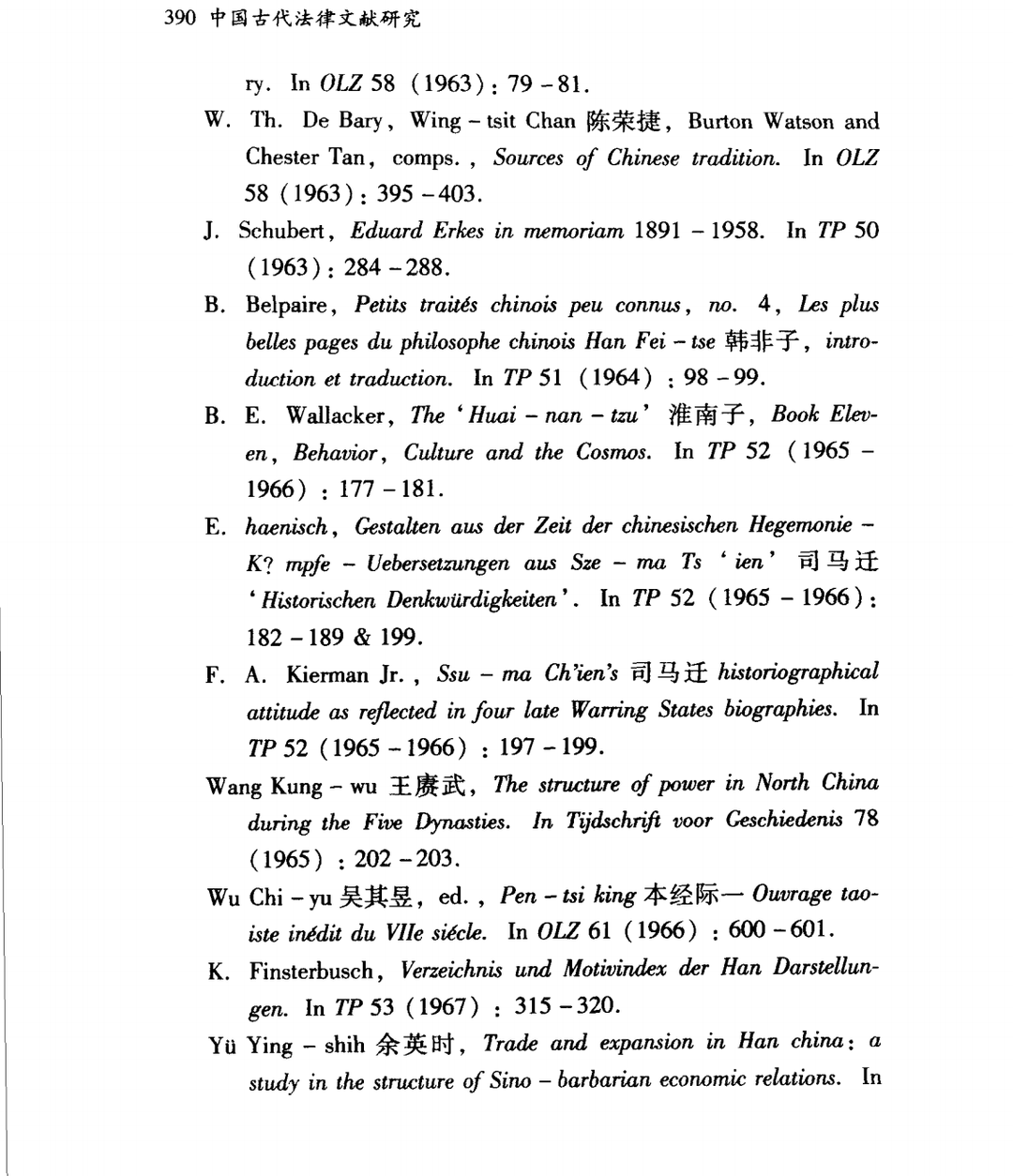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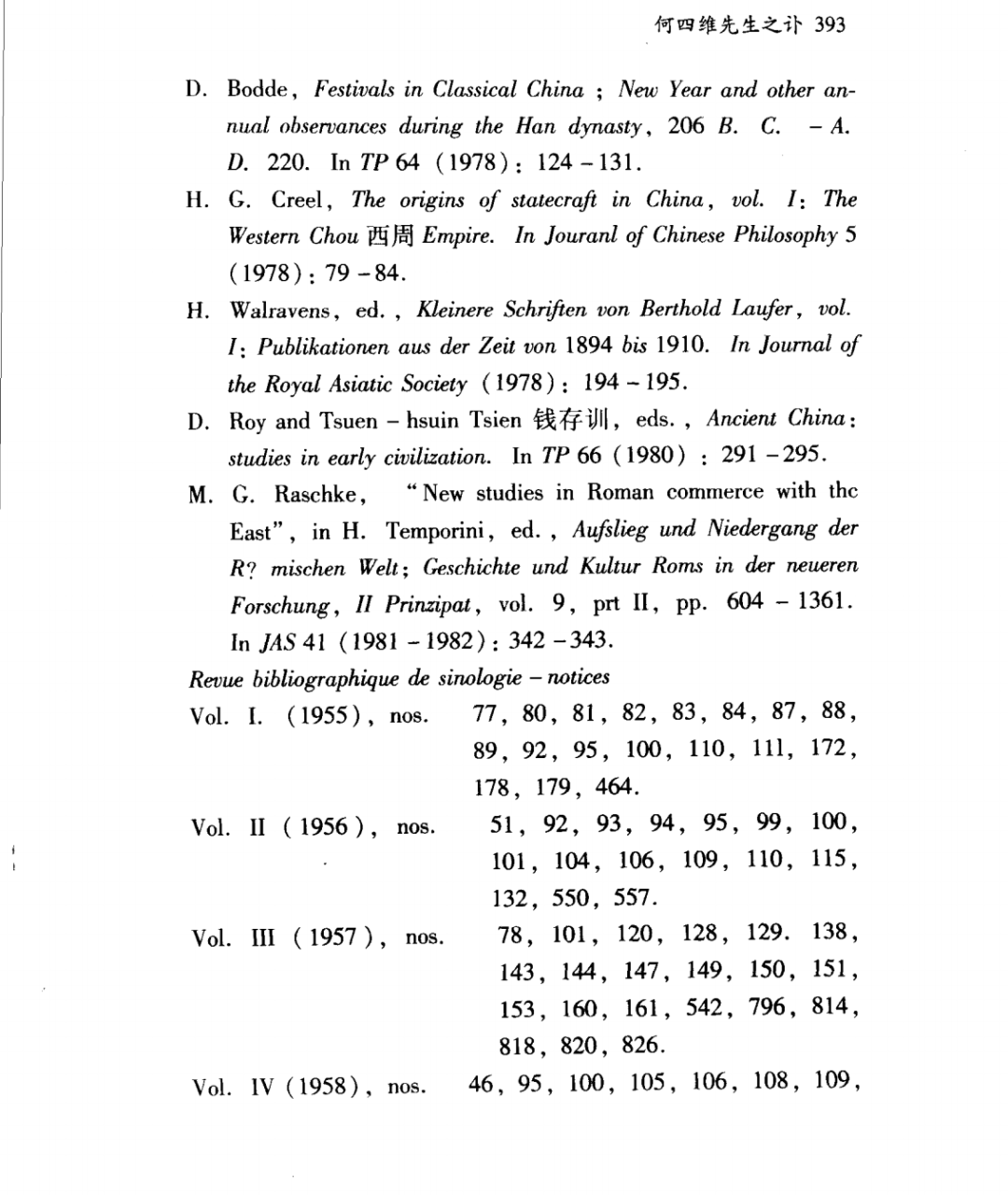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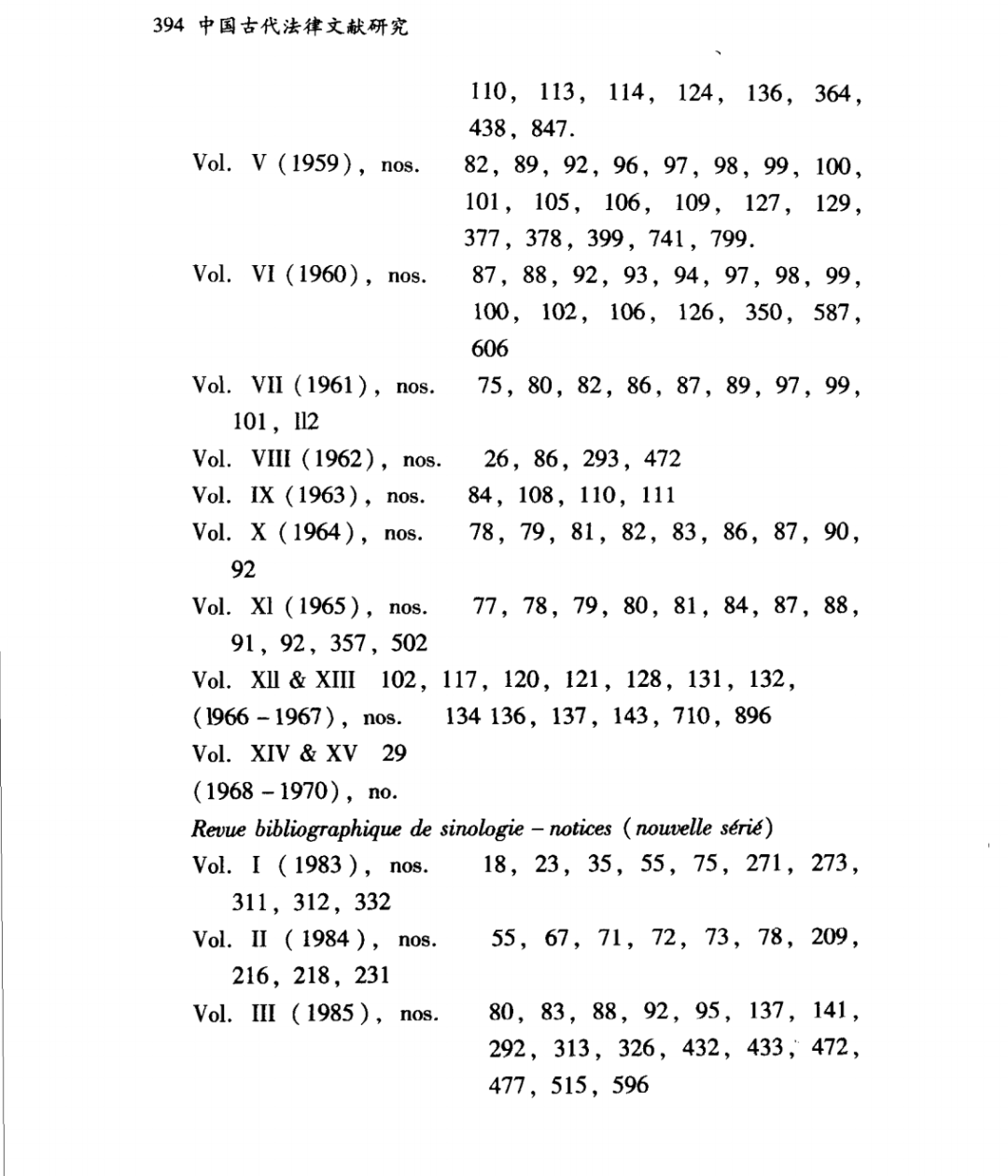

德尔•海尔编纂的何四维著作目录是罕见周到的个人目录,以此不仅可以了解到何氏的业绩,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欧汉学代表性学者的论著详目,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通览何氏的著作即可明白,秦汉法律制度是他明确的研究方向。作为汉学界的一名指导者,他在保持广阔视野的同时亦绝非散漫自流,到晚年他对自己的主题追求倾注了一贯的努力。课题的确定尽管有导师戴文达与友人范-德尔-瓦尔克的影响,但最终还是他自己的意志起到了决定作用,所以能始终执著于此,率先担当起帝制中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十余年殖民地官吏的经历,对于思想与文化素养皆深的他而言,也锲入到了他的法律制度研究之中,为他研究业绩的取得积蓄了力量。
“何氏之名保证了优秀文献学家的工作”,这是M.米耶(M.Meyer)对《秦律遗存》所作的书评之语(TPLXXXIIIVV,p.326),对此恐怕无人生异。从根本上看,何氏著作中也有不完全与失误之处,但从整体上看,他向国内外学术界提供的,无疑是极为诚恳的有用的基础研究成果°在《汉律拾遗》的书评中,滋贺秀三结合法典就七科谪(七种缺乏资格者)订正了著者的错误,又指出他对故意、过失法学理解上的不彻底性,总之对于在语言学、文献学上追求彻底的何氏的做法,表明了法史学家的不满。在文献学领域内,何氏认为现行的《史记•大宛传》是据《汉书》的《张骞传》、《李广利传》、《西域传》后出的。对此,榎一雄氏认为事实相反,正是《汉书》才出自《史记-大宛传》(见《东方学》第六十四期书评),此外“关于史记大宛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关系”(《东洋学报》六十四-一、二,一九八三年,第一~三十二页,后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一九九四年,第五十四~八十四页)一文也有反驳意见。此后未见何氏有相应的反驳。
对M.鲁惟一氏的报告,尽管何氏谦逊地表示鲁惟一是建筑家,自己不过是泥瓦匠(德尔•海尔氏所撰传记第十四页),但他那坚实稳健的素养有着充分的体现°诚如人们所知,他很快地仔细阅读了新出土秦简中的法制资料,对李学勤氏等人的工作有所裨益。在江陵汉简等新资料接连出土的今天,正是他所期待的大好时机,他的与世长辞实在是遗憾之至。我从内心期待着克罗、耶特氏等后继研究者继承他的事业,有助于推进他所开辟的领域。
从何氏的经历中也可发现,他对日语相当熟悉。一九七三年访日之际,在东洋文库的恳谈会上,他用日语平稳地介绍了荷兰东亚研究的状况。在介绍专攻中国俗文学史的新人可・艾德马(W.Idema)时,他在黑板上写了“出马”两个汉字,令我等听者吃惊,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故人对战争中日本的旧恶不记仇,尽力于两国学术界的亲密交流,缅怀其高洁的人格,从内心祝愿他冥福。
本文作者池田温,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创价大学教授
本文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原载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98页,注释从略。推送版本可能与纸本有所不同,若需引用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投稿方式说明
承蒙学界同仁的提携与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业已出版15辑,投稿方式如下:
来稿请以纸版或电子版方式,分别寄至:
(100088) 北京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编辑部
电子邮箱:
gdflwxyj@outlook.com
gdflwxyj@163.com
每辑的截稿时间为当年6月30日。
谨此奉闻,诚盼赐稿。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编辑部
欢迎关注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获取更多学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