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理希教授谈汉学生涯
编者荐语
-------------------
艾默理希教授与本所结缘,始于共同参加京都大学冨谷至教授主持的“东亚的犯罪与社会”课题,后又长期担任所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的编委。双方更于2016年签署了所际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交流。在他荣休之际,本所赵晶教授对他进行访谈,以为纪念。

莱因哈德·艾默理希(章静绘)
莱因哈德·艾默理希(Reinhard Emmerich)教授是德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长年精研中国汉唐之际的思想家,论域兼及先秦儒家、汉初黄老、隋唐佛教乃至于传统中国的酷刑、家族、国家统治等,曾主编出版《中国文学史》(Chine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Verlag,2004)。他长期担任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暨东亚研究所主任,曾兼任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并被遴选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科学院人文与艺术部院士。2022年9月底,艾默理希教授从明斯特大学荣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赵晶对他进行书面采访,请他回顾数十年研习汉学的历程。访谈稿由赵晶从德文编译成中文,并由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暨东亚研究所于宏博士审校。
采访︱赵 晶
您自1975年入学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以来,与汉学、中国结缘已近半个世纪。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呢?当时海德堡的汉学课程包括哪些内容?您又是如何学习汉语的?
艾默理希:主要因为我自己的个性:作为一名学生,尤其是高中生,我的兴趣点往往落在老师们不想让我关心的问题上,而非我“应该”措意的地方。因此,如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所撰《从马克思到苏联的意识形态:关于苏联、南斯拉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批判与史料》(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Darstellung, Kritik und Dokumentation des sowjetischen, jugoslawischen und chinesischen Marxismus)等课外读物开拓了我的视野,经常出现在高中课堂的课桌底下。而在我服兵役时,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的名著《中国人的幸福观》(1971年)出现了,没有什么年轻人能够不被它吸引。幸运的是,我的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
海德堡的课程针对的是古代中国,主要采用的教科书是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adick, 1902-1993)选文严谨、周详的三卷本《文言文入门》(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1968年)。
海德堡的德博(Günther Debon,1921-2005)以翻译《道德经》以及中国古典诗词而著名,他对您有影响吗?据说他对中国的兴趣源于在英国战俘营与汉学的接触,是这样吗?
艾默理希:在我眼中,德博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少数几位能够称得上“绅士”的人。他举止优雅,哪怕是对学医的年轻博士生,他也会尊称她为“大夫”;他与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那些与他违异的学生,则让其教学助理负责辅导。他极为低调谨慎,从不将私人的事情透露给学生,尤其是他十八岁应征入伍的早年经历、战争体验。至于他对中国的兴趣始于英国战俘营,并在那里遇到了杰出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这些都是传闻而已。作为学生,我倾向于相信并且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作为战俘时,科隆的艺术史学者史拜斯(Werner Speiser,1908-1965)向他介绍了东亚。由于他的个性、举止以及兴趣,德博在1970年代似乎就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其继任者、与他一样口才出众、极富魅力的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1941-2019)认为,他将一个坐落于城堡脚下、极富田园风光的海德堡汉学系提升为享誉世界的教学研究机构。这个机构自然懂得如何向德博致敬,继任者纪安诺(Enno Giele,1967-)在德博百岁诞辰的纪念上已有过恰如其分的表示。我个人则坚信,这位天才的翻译家、了不起的德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鉴赏家、笔名为Ernst Fabian的神秘诗人,将永远跻身德国汉学巨擘以及那个时代与世无争的个人主义者之列。我也希望,他的人生自白能被大家有感情地吟诵一下:“大概八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诗歌,知道它将伴随我的余生。有时候,它是能够最终保留下来的财富之一,因为它被藏在脑海中。”这引自其遗著《诗的特质》(Qualitäten des Verses)的序言,其中叙述了他在二战时的岁月。
您何时留学北京?对当时北京的印象如何?2014年10月,您在阔别北京三十余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对中国的印象有无改变?
艾默理希: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当时一则年轻,才读大学第五学期,二则基本没在海德堡学过现代汉语,所以语言能力极其有限,几乎无法应付学习以外的事情。那是1977-1978学年,并非我人生当中最安逸的阶段,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也是如此:谁能预料毛泽东、周恩来逝世之后国家将走向何方?对未来抱持怀疑、谨慎对待陌生事物,这似乎是普遍的生活态度。二十三四岁的我感受到了那种压抑,所以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并决定今后的研究不会聚焦于现代中国,这个选择是我下意识的决定。之后,中国经历的变化被世人一再提及。就个人而言,没能在2014年以前再访中国,我始终深感遗憾。回首前尘,真希望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些发展。

2014年10月8日,艾默理希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09主讲“德国有关前近代中国的研究”。前排就坐者,从左至右分别是徐世虹教授、艾默理希夫人、艾默理希教授、充当现场翻译的金晶讲师(当时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艾默理希夫人身后站立者是采访人赵晶。
1979年,您入学汉堡大学,那里有德国最早的汉学系,名家辈出,当时在任的教授有拉尔(Jutta Rall-Niu,1929-2006)、毕少夫(Friedrich A. Bischoff,1928-2009)、司徒汉(Hans Stumpfeldt,1941-2018),分别研究医学史、文学、思想史。您选择汉堡的原因是什么?
艾默理希:我一直成长在一个淳朴的环境中,与家乡以外的世界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学年。在那里的学习过程中,我萌生了扩大视野的愿望。选择汉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汉学领域的名气,包括一些如雷贯耳的人物,如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刘茂才(Liu Mau-Tsai,1914-2007)。事实上,1978年下半年,在我了解到这个汉学系时,它已然式微,因为傅吾康已经退休,刘茂才行将退休,他们都后继乏人。不过,我仍然决定留在那里,更加发奋自学。这个决定成就了我。
您曾合作主编司徒汉六十五岁贺寿文集(Friedrich Michael, van Ess Hans, Emmerich Reinhard [Hrsg.]. Han-Zeit: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umpfeldt aus Anlaß seines 65. Geburtsta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6),并撰写关于他的回忆文章("Hans Stumpfeldt [1941-2018] in memoriam", Oriens extremus, 2018-2019 [57],2020),由此看来,您应该受他影响最深吧?能谈谈对他的印象吗?
艾默理希:1979年,我被司徒汉招至汉堡,学生生涯因此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向:他是一位“工作狂”,兴趣极为广泛且头脑敏锐,不满足于接受既往成说;他采用的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类似体验;在读博期间,我有幸与他共事无数个日夜,这对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而在我担任助手期间,他给了我所有能够想到的自由。在汉堡,另一位汉学教授在许多方面与司徒汉有别,他就是你提到的毕少夫。无论是在个人行为上,还是在教学中,这位奥地利外交官的哲嗣都会流露出世界主义的倾向,再配上他那倍加犀利的讽刺,以及孜孜不倦地追求不同寻常、无所顾忌的解释。此后我未再遇到过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家。
您最早发表的学术著作是与爱伯斯坦(Bernd Eberstein,1942-)等合译的康有为《上今上皇帝书》。傅吾康的博士论文就是康有为与维新变法。当时译注此篇的考虑为何?
艾默理希:这是爱伯斯坦决定的。在我看来,在前述傅吾康、刘茂才退休后的转型期间,爱伯斯坦为维持汉堡汉学系、维系学生群体做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
当时两德分立,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在一次访谈时称,联邦德国受1968年运动的影响,汉学家普遍不重视母语,而民主德国的汉学家则重视德文的表达与修辞(《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第276期,2009年12月2日)。您对此有何看法?
艾默理希:顾彬喜欢作惊人之谈。如果他说的是,那些学者在使用非母语表达时,思想有平庸之虞,那么我可以表示赞同;如果他说的是,科学的写作可能、也确实应该追求文雅的表述,那么我也同意。
您在硕士阶段的研究主题是什么?198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以李翱为主题,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您于1988至1994年间在汉堡大学担任研究助手,主要是撰写教授资格论文吗?当时研究贾谊,后来又研究王充,为何会从唐代转向汉代?
艾默理希:选择研究主题,既有偶然因素,也是对学术体制的一种妥协。钻研李翱是与司徒汉讨论的结果,硕士论文的选题也是如此。不过,硕士论文是在1981年的暑假仓促完成的,当时为了拿到一笔读博的奖学金。至于我在写完博士论文后选择离开唐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因研究领域过窄而无法在德国的大学谋得一个教职。哪怕是现在,类似的不成文规矩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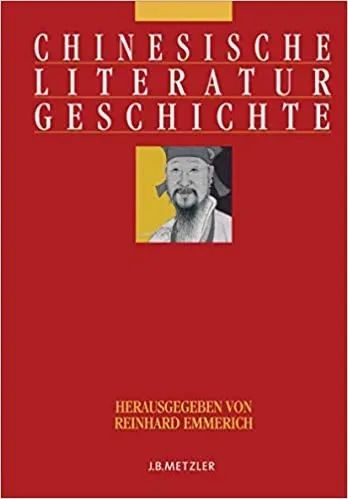
艾默理希教授主编《中国文学史》书影
1985至1988年间,您前往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留学,当时的接待教授分别是谁?
艾默理希:此生最大的际遇之一,就是著名考古学者林巳奈夫(1925-2006)欣然接受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博士生,让我有机会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这让我有幸了解到共同研究班和整个研究所的文化:让所有成员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若干年后我又意识到,对于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多么重要。1985-1987年在京都的经历还有更加重要意义,那就是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较为年轻的汉学家。在我任职明斯特的这些年,这些友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互相之间的密切合作已不再局限于我个人。就我个人而言,与冨谷至(1952-)的相识是十分关键的,他是我相知多年的亲密友人。

2014年3月23-25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明斯特大学汉学系在京都合办“Crime and Morality in East Asia”研讨会。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永田知之准教授、冨谷至教授、艾默理希教授。
留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与第一次留学日本一样,也很偶然:我曾读到鲍则岳(William G. Boltz,1943-)的一篇论文,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写信给他,得到了他的邀请。而当自己有机会师从鲍则岳以及享有盛誉的司礼义(Paul L-M Serruys,1912-1999)、康达维(David Knechtges,1942-)时,我逐渐了解到西雅图的汉学研究有多么出色。总的来说,鲍则岳在1988年的接待访问可能对后来的德国汉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他此后数次访问德国的大学,尤其是明斯特、汉堡,以及柏林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与不同研究者多所交流。
刘子健(James T. C. Liu,1919-1993)曾在《国际提倡宋史的“史话”》中回忆到,1971年在德国的费尔达芬召开宋史会议,参加者有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会后编辑论文集,主编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辈的论文(转引自宋晞:《刘子健先生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宋史座谈会刊印,1994年,24页)。当时德国汉学界对日本学界的态度如何?
艾默理希:1971年的汉学界并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我无法回答这个方面的问题。不过,我很难想象那时的德国或欧洲汉学家对日本学者会有本质上的蔑视。作为一个学生,我总是听到对日本汉学的最高评价,尤其是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当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隔绝状态时,那里就是德国、欧洲汉学家首选的留学地。
您遍访中国、日本、美国,与相关学人皆有往来,在您看来,不同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教学方式与研究路径各有何特色?
艾默理希:对此,我不想、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下拟指出四点:第一,中国学者在处理古代的写本史料时,他们最终面对的还是自己的母语,因此不是非得进行翻译。他们寓目的史料远多于欧洲学者,而且在解读这些史料时,他们也比欧洲学者更注重细节。第二,欧洲的汉学家说到底还是站在比较的立场上,无论他们是否学过汉学以外的其他科目。第三,中国学者常常只检讨汉语成果,包括用汉语撰就的和译成汉语的。欧洲与美国的汉学家则会努力搜罗不同语种的专业研究,虽然一个可见的趋势是,美国的汉学家在汉语、日语研究之外,也只参考英语文献。第四,在大学的日常教学中,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同行,德国汉学家的工作范围通常会更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也胜于美国同行。因为学生的兴趣极泛,教职人员的数量又极为有限,而且学生在进入大学时,是在毫无或仅有一点相关知识的情况下投身中国研究的。
1997年起,您接替荣休的翁有礼(Ulrich Unger,1930-2006),入职明斯特大学汉学系。夏含夷在《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中专门为翁有礼写有小传,把他归入“西方汉学金石研究”脉络之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从未到访过中国,论著也限于内部分赠(而非公开出版),因此中文学界对他知之甚少,您在2019年主编出版了他的《古代汉语语法》(Grammatik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 Berlin: Cross Asia E-Publishing),能否再介绍下其人?
艾默理希:翁有礼一生并未去过中国,德博也是如此。对翁有礼而言(也许德博也是,但我无法确定),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一定是,他感兴趣的中国已成过去,接触新的中国或许无益于他的学术研究。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态度,而且许多在中国有过经历的老一辈汉学家也确实对此感到奇怪,不过我仍然认为,这种态度理应得到尊重。一名研究者对某一文化的古代阶段感兴趣,当他直面该文化的现代阶段时,他会有什么收获呢?根据典型的个案,对此加以探讨,应该会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也许最后的结论是,避免这种古、今比较会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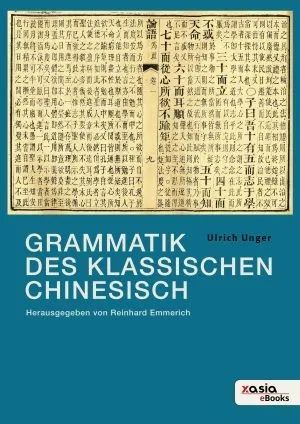
翁有礼著、艾默理希主编《古代汉语语法》书影
明斯特大学汉学系成立于1962年,林懋(Tilemann Grimm,1922-2002)为首任教授。林懋师从傅吾康,与您都是汉堡出身。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他与明斯特汉学的渊源吗?
艾默理希:是的,林懋在汉堡师从傅吾康,而且接续其学统,在明代研究上做出了影响卓著的贡献。比起傅吾康,林懋因其父亲在中国(北京和天津)行医(耳鼻喉科和眼科),而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其成长的家庭环境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被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质所感动”(Nachruf auf Grimm in NOAG 173-174.2003, S.5),这些可能对他有更多的影响。1962年,他受聘为明斯特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不过仅仅在此执教三年,就转任1962年才成立的波鸿鲁尔大学。如其讣告所言,在那里,他“醉心于背景更加广泛的、跨学科的东亚研究所”(NOAG 173-174.2003, S.6),而且越来越将关注点转向了现代中国。如前所述,林懋在明斯特的继任者是一位与他在背景和兴趣上截然不同的学者。
明斯特大学汉学系原本一直坚持“古典汉学”方向,但近年来整个德国汉学界的主导风向是专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艾默理希:明斯特汉学的关注点依然是传统中国。而且相较于以往,我的继任者在研究与教学上所承担的任务会更加侧重传统中国,这是因为这所大学想将汉学与其他学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大学管理层的一个明智决定,尤其是他们还决定另外设立一个教席,负责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你所提到的以及翁有礼教授所热爱的“古典汉学”,在德国的大学中依然有相当的代表性,更遑论美国。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激起年轻人对它的兴趣,只要实用主义思想没有在大学主事者那里占上风,那么就不会损及古典汉学的未来。当然,如果我们在大学里讨论放弃研习传统中国而转向现代中国是否更加有用,那就很不幸了,那时我们都将失败。洪堡曾提醒道:科学需要持续性,且有时毋需被拷问目的。
著名汉学家、法学家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1903-1997)留下了一部《唐律疏议》德译本的手稿,现在由您负责整理。众所周知,宾格尔因与纳粹有关,所以在二战后颇不得志(参见江玉林:《“守法”观念下的唐律文化——与Karl Bünger〈唐代法律史料〉对话》,黄源盛主编《唐律与传统法文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在《德国的汉学研究史:历史、问题与展望》中也提到“当年留在纳粹德国的学者们的政治角色,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并以无人撰写汉学家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的传记为例(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28页)。您对于这个话题有何看法?
艾默理希:是的,宾格尔与颜复礼都是纳粹党成员。就宾格尔来说,目前还是无法拿到与他相关的档案,在这一方面也不能以讹传讹。宾格尔似乎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1947/1948年从中国被遣返回德国后在遣返中心逗留数月。由此可以假设,这是他后来出任外交官的前提条件。我无法断言他是否因此而不受欢迎,不过想引用一段早年间傅吾康在中国遇到宾格尔后对他充满敬意的评价,来自傅吾康1941年5月1日写给父母的信:“我也非常欣赏宾格尔,虽然他有些枯燥乏味,但性格安静自然……他实事求是,有很好的判断力。对中国事务的理解大概比我们大多数在中国的政府代表要多得多——尤其是政治方面——因此派他来这里非常受欢迎。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知识渊博而有自己的判断,不需要将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 S. 138;以上汉译,参考傅吾康著,欧阳甦译:《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44页)
至于颜复礼,他自1905年以后一直在慕尼黑和罗斯托克学习古典语言学。在1910年于汉堡跟随福兰阁学习汉学之前,他已获得了博士学位(最高分)。福兰阁对他颇多鼓励,无论是在专业上,还是对其个人,都称赞有加。在颜复礼就读的一年后,福兰阁就为他申请了助理的职位。颜复礼于1935年受聘为教授,接替其师福兰阁,当时汉堡大学的校长对他是纳粹党员表示赞赏。1945年8月,英占区政府暂停了他的职务;1947年4月,他恢复原职,担任全职教授以及中国语言与文化系主任;1947年6月,他的离职申请获准;1955年1月,他获得荣誉退休教授待遇。傅吾康曾评价道:“颜复礼本质上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很好说话,他经人说服,不但入了党,还接受了一个教师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实际上他完全不适合后一项工作。”(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I, S. 9;以上汉译,参考傅吾康著,欧阳甦译:《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97-198页)
与纳粹党员相关,我们可以,也必须提及那些受命运眷顾、免于入党的人。其中就有傅吾康,在战争年代以及二战前后(1937-1950),他被允许留在中国,后来又接替了颜复礼的职位,后者虽是纳粹党员,但并无政治上的过错。在其回忆录中,傅吾康承认自己曾受德国军事胜利的影响,于1941/1942年递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但似乎在北京与柏林的通讯中丢失了,这份坦诚令人动容:“在各个前线的巨大军事成功之后,看起来德国人可能赢得战争而纳粹仍会执政。那么,可以预见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不是党员,不管能力和成绩如何,就只能满足于高校中一个下层的终身职位。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也胜任不了反抗斗争。我和中德朋友们谈及此事,他们多数人建议我入党,特别是胡隽吟(1910-1988,她后来成为傅吾康的太太——艾默理希注)认为,这不是太原则性的事儿,仅仅是一个形式,只需从实用的角度来对待。”(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 S. 123;以上汉译,参考傅吾康著,欧阳甦译:《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129页)
我想应该结束这个话题了。或许某些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当拷问祖先时,自己又能够承受多少政治与社会压力?无论如何,我在生活中也曾遇到过一些懦夫,他们只要有一丁点儿勇气,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誉损失了。
部分德国汉学家似乎与法学有不解的渊源。除宾格尔外,如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也曾学习法学,甚至获得法学博士,他们都算是外交官。您觉得法学训练是否让他们的汉学研究别具特色?
艾默理希:我无法评估法学训练对佛尔克的影响,但对宾格尔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在二战之后重塑德国汉学、风头一时无两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也是如此,他首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1937),之后才是汉学/哲学博士(1947)。我认同以下这种观点:法学训练能够强化一种严谨提问的能力,这是超越法律本身的,就像学习拉丁文有益于文本理解一样。最后,至少在德国,像佛尔克、宾格尔、傅海波等拥有法学学位的人,在人文领域都是通才,这也是从事外交职业的前提条件。即使是成果丰硕的汉学教授傅海波,也曾短期从事外交工作,1953-1954年间曾出任德国驻香港领事。

2019年7月27日傍晚,明斯特大学汉学系举办艾默理希教授六十五岁颂寿庆典。
您在明斯特汉学系执教二十五年,已经于去年秋天荣休。卸下沉重的教学任务后,或许更能悠游自在地研究学问。未来您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艾默理希:我非常荣幸地接到邀请,在退休后重返海德堡,担任了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几十年前我在那里曾度过了初识汉学的一段时光,现在又体验到了与明斯特汉学系有所不同的系内状况。我想自己暂时还不会完全失去一直所享受的教学相长之乐。至于此后会如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箧笥之中充满了已然动笔的未成稿,但我还是不断地对新事物产生兴趣。另外,我还有两个愿望:其一,保持身体健康与工作活力,以便见证中国的持续发展;其二,在我淡出学界后,中国政法大学与明斯特大学的友好关系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